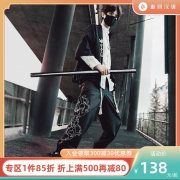【汉服杂谈】来自《新周刊》的疑问:何谓汉服?标准是什么?
摘要:黄帝时期,华夏衣冠(汉服)诞生,处于幼苗阶段,主体是衣裳(裤)制。
何也想象不出地球上曾经存在过18米高的巨型动物。
“大象无形”,一般没有深入了解过的人们有着零碎的刻板印象,无法从表面印象中去把握本质特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做出非常多的努力,去重构现代汉服形制体系,以及重构社会对现代汉服的思想观念。
既然已经知道古代汉服的发展史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性过程,由于历史原因,中间停止发展了数百年,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重建现代汉服体系,就相当于说,重新栽种一棵树苗,重新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而且这棵树是深深扎根在大地里,不是供人品鉴的案头小物。
那么这里就必须回答《新周刊》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何谓汉服?标准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的观点和论述。本文认为,现代汉服不同于古代汉服,是需要重建现代汉服体系,根据今天的时代需求进行筛选和重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现代汉服与古代的汉服具有一脉相承的同一性?
古代汉服是客观存在,但是已经死亡了,是一种历史资源;现在是在历史资源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废墟上重建,那么显然需要把握本质上的东西才算继承和发扬。
从总的宗旨来说,大家都知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笔者对此的解读是:“取其一脉相承的整体框架,弃其古代过于突出的时代特征”。
在谈标准之前,需要理清一个观念,汉服体系包括了人生礼仪、社会交往、情感寄托等各个层次的服饰文化,是大小传统的综合体。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是什么?这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观念冲突,或者说观念脱节。
在汉服研究者或实践者看来,汉服具有礼仪功能、社交功能等等实用功能;而在社会大众等围观群众看来,汉服仅仅只有美化功能或者某种身份标识功能。大众非常疑惑:
为什么要穿古装?为什么要穿戏服?为什么要当街进行角色扮演?
这里就涉及到一些更为宏大的元问题,比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论。既然定位是现代汉民族传统服饰,那么就是现代中国的文化,而非西化中国的文化。从这里来看,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人穿现代服饰,既包括了现代化后的西方服饰,也应该要容得下正在现代化的传统服饰。
这里提到的“正在现代化”,意思就是建构现代汉服体系是一个进行时态,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哪里有一来就完美无缺、高度完善的?这不是一个一阵风式的商业运作,而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无数人呕心沥血践行的社会课题。
建构,则意味着主动地建设,而非被动地复制过去。本文认为,今天我们在确定标准汉服标准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去朝代化,也就是努力地去掉某个朝代的突出特征,不要让这些朝代的时代痕迹遮蔽、淹没了其本质特征。其次是避免“唯文物论”,一定要避免将具体文物作为唯一的至高标准。总的来说,就是要避免2种路径依赖:
1、文物仅仅是十万、百万不存一的凤毛麟角,就好比是一片树叶和一块花瓣,我们怎么可能以树叶和花瓣种种具象作为重构“树木”的标准?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你掉落的头发、剪掉的指甲和切掉的阑尾,都是你身体真实存在过的一部分,都是你真实的历史事件记录者,甚至携带着你所有的基因信息,但是可以说掉落的头发、剪掉的指甲和切掉的阑尾是判断你这个人的唯一、至高的标准吗?甚至可以通过掉落的头发、剪掉的指甲和切掉的阑尾等等表象特征来规定和定义你这个人吗?
2、不同朝代根据当时的时代需求发展出非常具有特色的款式,比如曲裾深衣杂裾飞纎圆领袍,比如直身道袍凤冠霞帔飞鱼服等等等等,这些有名有号的款式,都需要进行“去朝代特征”之后,剩下的本质特征,才能纳进现代汉服体系的建构中来。当今天穿着一身圆领补服加漆纱幞头出现大街上晃荡时,你很难说服大众,你不是在穿戏服搞角色扮演游戏。当朝代特征或者封建社会的阶级特征过于强烈,以至于遮蔽了文化本身超越时代的本质部分,那么这种文化宣传起到的往往是反作用。
笔者的观点是,需要先打破长久以来笼罩在我们自己心目中的定势和刻板印象,从历史角度出发,打破唯文物论,去朝代化,建立整体性的体系概念,建立起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范式”,建立起“正在现代化的传统文化”的意识。
大方向是去掉朝代特征、尽可能实践一些带有共性的东西,把贯穿几千年的共性作为反复出现的题材来用力,反复就一些带有原型色彩的基本款进行发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很多年以后回答《新周刊》关于没有标准的问题。
目前各种晋制、唐制、宋制、明制是必经之路,不可能回避,这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对中国服饰史的印象就是鸡零狗碎、一个朝代一种款式,本身只了解到最突出最有时代特征的几种款式或形象,对于“大象”的其它部分,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盲人摸象:我说大象像一根绳子,你说大象像一把扇子,他说大象像一根柱子(然后有人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大象,大象是伪概念,是商家的文创作品)。但是不可能强求大众在研究文物文献之后再去穿衣服实践,所以只有在高涨的热情中不断实践,来反复推进对整体性的认知和研究。
笔者在前一篇文章《拿走不谢!如何优雅地回答“穿汉服不如多读书”?》主要辨析了形式与内容(精神),其实还有一个小尾巴,那就是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承载我们所要宣扬的精神?
这个“形式”在具体说法上,应该叫“范式”。因为我们去掉了朝代的特征后,去努力把握本质特征的时候,会用到抽象的能力。在这里笔者不去展开谈抽象的哲学原理,只谈我们不讲具体文物,也不讲朝代特征之后,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剩下的有可能是空洞的概念,也有可能是“范式”。
假设我们避开了一切的陷阱,抓住了本质,形成了“范式”,那么我们可以愉快地讨论关于汉服的一切问题。就好像我们可以毫无阻碍地讨论“马”、“桌子”和“大树”。
当笔者提到“桌子”这个词汇,大家心目中就显现出来了一个心理图形。心理图形是不可以具体描摹出来的,一旦绘制出来,就是该概念的具体殊相。虽然不可以描摹,但是大家都清楚“桌子”的归类标准,都知道判断的边界,都知道应用的方式。
由于在消亡期,不可以合法穿着汉服,出现了物质层面的断层,从而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断层,也就是汉服的“范式”消亡了,大众的心理图形消亡了,这种断代是毁灭性的、根本性的。今天汉服运动在做的事情,就是从物质层面恢复,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大众思想观念上重构汉服的心理图形,也就是“范式”。
举一个例子:
“交领右衽”是比较早期取得共识的一个“范式”元素,比如说“中国华服日”的LOGO,就是取自这个意象。说明在人们心目中,这个形象不管是长袖短袖、不管是长袍还是短衫,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心理图形。

当然,“交领右衽”是汉服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征,已经开始在今天社会上形成了初步的范式(并不是说凡是“交领右衽”的衣服都是汉服,更不是说汉服就只能是“交领右衽”)。还有大量的基础形制和款式(比如衣裤制)没有形成共有的印象。提出物质层面的细节标准到最后形成共有的范式,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
因此,现在还不到回答有无标准的时候,可能需要等历史上出现过的衣服款式经历完几个潮流轮回;暂时不能回答,并不是说汉服没有标准,而是因为汉服体系过于庞大,断代过于久远,需要较长时间来实践、思考和生长。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们播下的树种已经发芽,郁郁葱葱,接下来就需要精心培育,让它重新长成参天大树。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历史阶段,有足够的信心,未来将会是一整片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森林。

 穿着汉服上街 还要带着汉服去旅行
穿着汉服上街 还要带着汉服去旅行 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莫言:宽衣大袖自风流
莫言:宽衣大袖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