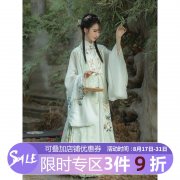汉服运动:从民族愤青到二次元萌萌哒
摘要:除了一位身着宽袍大袖,头戴发簪,固执地跪坐在蒲团上的男士,我和这些汉服青年几乎都是在咖啡馆见面的,点的分别是茶,奶茶,拿铁,摩卡,匹萨饼。咖啡机轰鸣着,制造出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轰响和醇香。
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叶宏明解释说:"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语是中国的'国语',因此确立汉服为'国服',既代表了汉民族的传统,体现了汉文化的历史沿革,又能增强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侨同胞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当时的复兴者们看来,汉服登上"两会"提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4月,网上出现了联合倡议书,倡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用汉服"深衣"作为礼仪服饰。
2007年8月的央视节目《实话实说》,讨论奥运会礼仪制服和运动员入场服装,汉服,旗袍和现代时装都在备选之列。38分钟的节目里,汉服青年显然并不愉快。"会不会不方便?"这个问题至少被问了三次。
台上的人有些焦躁了,她提高了音调,试图辩解:"你觉得不方便是因为你没有穿过。在我穿上汉服之前,我和你有同样的想法。"
主持人哈哈笑着,试图圆场。
当时在观众席上做"人肉背景"的黑猫,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有些愤懑:"他们故意找嘉宾来怼我们。"
现实令人挫败,而一些复兴者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2008年10月5日下午,历史学者阎崇年在无锡签名售书会上,遭人掌掴。阎崇年曾在CCTV百家讲坛上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和《明清兴亡六十年》,而打人者"大汉之风",并不将这次事件定性为"学术之争",在被拘留半个月释放后,他对媒体表示"不后悔,不道歉","打他之前我没考虑任何目的,只觉得是正义对邪恶的反击。" 阎崇年关于"剃发易服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的言论,显然冒犯到了这些复兴者们的"政治正确"。
直到如今,这种"政治正确"依旧有人承下衣钵。吴化之是"华夏文化研习会"的负责人,他是那种说话有很多宏大概念的人,时而引经据典。他蓄发,饮茶,每天穿汉服。因为最近感冒,他又在汉服里添了一件衬衫。

他和三位"研习会"的工作人员一同住在位于居民楼的办公室里。大厅正中是茶席,靠窗位置摆着一圈沙发。他们有三排书柜,书很杂,从《史记》到《国富论》,从《汉武帝大传》到《组织行为学》,在中间书架的第四排,还摆着一本《货币战争》。
吴化之对清朝保持极负面的批判态度,他甚至把"中国人崇尚金钱和强权"归因于满清政权的统治。在2010年接触到汉服时,他觉得自己被"唤醒"了--那些让他尊崇的汉服复兴运动前辈们都是"悲情"的。他仍旧坚持把汉服置于神坛之上,但近来新加入的同袍们似乎让他不那么满意:"汉服运动一开始事实上是正本清源,现在随着时间发展,大部分人不知道汉服运动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就变成没有主张,没有核心价值观,没有真正崇高理想的,纯粹穿着汉服的普通人。现在汉服运动也面临这个问题,已经被虚无化了。"
至少在2008年之前,大秦的观点和吴化之有着一些共同点。当时,汉网和吉祥满网两家论坛的网友,总是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大秦跟一位满族网友线下约着见过。在来之前,那人的女朋友还劝他别去,怕跟大秦见了面会被打。大秦带了两个人来,都是汉服同袍。架没打,四个人只是约着吃了顿饭,"都是文化人"。双方就历史问题还是难以达成一致,大秦觉得清朝强制剃发易服断了汉服三百年;后者将入主中原视为祖先的荣耀。饭吃完了,谁也没能说服谁。
大秦身材高大,一位认识他的网友形容说,他的脸长得像秦始皇兵马俑。采访那天,他穿着一件交领长衣,不仔细辨别,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件时髦的大衣。他记得第一次见到汉服的报道,是在2003年北京电视台早间新闻上。三年后,他惊讶地发现,在网上,这个群体已经变得相当庞大。退伍后,大秦成了一名婚礼策划,专做汉式婚礼。他崇尚秦人,推崇务实主义,钻研两年西式婚礼后,他把现代婚礼的灯光舞美又用回了汉式婚礼上,因为"好东西是没有国界。"北京汉服同袍的婚礼,多半都是他来操刀。

可无论是身份证上还是祖上,大秦都是回族,上幼儿园时回家讨火腿肠吃,他还被姥姥教训过。而那场和满族网友的饭局,四个参与者里没有一个是汉族:"他是满族,我是回族,这边一个胖胖的小丫头是白族,这边的女孩也是满族,正白旗的,只不过身份证上是汉族的。"
2006年汉服青年与《竞报》的那场官司上,大秦戴着回族小白帽,以回族的身份出庭作证。事后,这却在汉网上给他引来了攻击和微词。
大秦自称是"炎黄子孙",尊重汉文化。在他看来,汉式婚礼乃至于汉服推广,需要去汉族概念,突出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他举了个例子:"汉字汉语只有汉族人能用吗?不是,它是整个中国都在通用的语言。"
大秦的想法代表着这场复兴运动中很多人的观点。在这一部分人看来,那些悲情满怀者早就落伍了。2003年汉网上激烈的汉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很难说服这些伴随着网络和全球化市场成长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是从全世界涌入中国的科技,电影,食品,服装和思想。他们更乐意使用"找寻"这样的词汇,似乎要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到能与强大的西方文明相对应的存在。
2009年,三月初三,上巳节,这群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们聚集在玉渊潭公园。那天,不是所有人都身着汉服,在电商还未把触角扩展到千家万户时,很多人的第一套汉服都需要自己动手。如今成为吧务组副会长的魁儿说,她是在那场活动上第一次穿上汉服,"就一种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对,真的是穿上汉服的一刹那,你感觉一下子就找到了什么。" 她今年24岁,个子娇小,一根发簪把长发固定在脑后。我们约在海淀区一家咖啡馆见面,聊汉服的间隙,她会嚼两口披萨。她因写小说与汉服结缘,自2009年吧务组成立,几乎一直全职承担汉服北京的事务。同很多90后的同龄人一样,她逛漫展,看网文,追日本动漫,比如《火影忍者》和《元气少女缘结神》。
"我们的三观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包容的心,去宣传传统文化,同时也呼吁其他民族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但是现在的社会在慢慢淡化民族概念,所以我们也不太去提,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团体里有激进的人。" 她说。这些"激进的人"指汉民族主义者。
一些人抵制"汉服圈"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们被框定在一个狭小的区域,远离主流人群。但在更为广泛的公众眼里,这种着装方式显然未能成为一种主流。
"如今,虽然它依旧归属于亚文化,属于非主流,但是这十三年来,从无到有,从一片反对与质疑,再到部分被接受与人口,已是今非昔比。"在《汉服归来》一书中,杨娜写道。但在很多汉服青年看来,他们与网络时代发展出的亚文化群体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cosplay,萝莉装爱好者。
"现在的二次元妹子融入进来之后,她们注重的就是这个衣服漂不漂亮,就不是那么注重一些细节了,比如说穿汉服不应该披头散发。"魁儿说。

被加诸衣服上的符号,在变幻莫测的网络时代中不断遭到消解,成长于网络时代的汉服同袍们也在经受更加年轻的群体冲击。较之2003年的前辈们,这些后来者似乎天生带有后现代的解构气息。新的同伴带进来了更多新的概念,比如"入坑出坑","退圈了转卖衣服"。他们通常更关注服装的外观,在网上,一般被称为"秀衣党"。在很多汉服青年的眼中,"秀衣党"是要被排除在外的,抽离衣服的具体款式和传统文化的外衣,他们的行为逻辑与cosplay基无区别。
桃木并不清楚在这个群体中,"秀衣党"不算什么正面的存在。但按照严格的定义,她也不算"秀衣党",因为她仍旧注重衣服的基本形制,并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的影楼装。
桃木曾经担任学校里汉服社团的社长,除此之外,她的身份还有动漫社前成员,《剑侠情缘叁》玩家,《阴阳师》玩家,cosplay爱好者。在被问到cosplay装和汉服必须丢掉一件时,她思考了一会,说:"cosplay。"因为汉服可以日常穿,但cospaly装不会。在衣柜里,汉服和牛仔裤是同样的地位。
第一套汉服是父母帮忙买的单。父亲觉得无所谓,母亲却有些微词,因为"玩汉服是玩物丧志"。她显然更希望考上名牌大学的女儿能够把精力放在专业上,"对你未来就业有用。"
见到桃木时,她正在帮社团招新,穿着一整套袄裙,宝蓝色上襦,大红色裙子,即便身处嘈杂的咖啡馆里,仍旧引人注目。于是在采访刚开始没多久,一个男孩冲上来问:"同学,你们cosplay社怎么参加?"
"这是汉服,不是cosplay。"像是回答了数千遍,桃木熟稔地回复。
"有情侣装吗?"男孩身后是一位怯生生的女孩,他们商量了片刻,还是由男孩开口。
"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汉服社。就是看自愿,你愿意穿就穿,也不强求的。汉服有很多店家专门做情侣装的。可以在我这里报名。"
他们双方加了微信,或许这对情侣真的会报名参加汉服社。
在之前的采访中,我几乎问过每个人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看"秀衣党"?除了那位担心陷入"汉服运动虚无主义"的情怀者,其他人对这个群体也没有什么负面评价:"在汉服复兴的时候,我们恰恰也

 穿着汉服上街 还要带着汉服去旅行
穿着汉服上街 还要带着汉服去旅行 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莫言:宽衣大袖自风流
莫言:宽衣大袖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