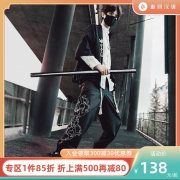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下)
摘要: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春雪体,深涧择泉清处洗,殷情十指吐蚕丝,当窗袅袅机声起,织成一尺无一两,进贡天子五月衣。”生动地描绘了当地所产葛布的精美。入唐以后,丝织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并且成为当时上贡丝织物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所产丝织品的品种,则数第一。史载自贞元(785—805年)以后,越州“凡贡之外,别进异纹吴绫及花鼓歇单纱、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其中缭绫,尤称精绝。白居易《新乐府·缭绫》诗有:“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可见当时浙江一带的丝织已相当发达。
浙西还出产一种盘绦绫,有玄鹅、天马、掬豹等多种花样,罗娟也很精致。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宰相元载的宠姬“衣龙绢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抟(tuan)之不盈一握”。宣州丝织可与吴、越比美,上贡的红线毯最为名贵,其特点是:“采丝茸茸,线软花虚”,不象太原产品的涩而硬,不似成都产品的薄而冷。为此宣城太守强迫人民大量织造红线毯进贡,以博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诗人白居易写《红线毯》诗进行痛斥:“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种名贵的丝织品,虽属贡品,但也说明了东南一带的织工们掌握了较高的丝织和染色技术,丝织生产有了显著发展。因此,唐人流传着:“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来形容长江流域蚕桑丝织之盛。
蜀锦历史悠久,到隋唐时期,蜀锦仍很有名,花式品种仍在不断发展。诗人郑谷赞美当时蜀锦上的花鸟、云雁生动活泼如:“春水濯来云雁活”。代宗时,敕令禁织的贡品就有:“大张锦、软锦及蟠龙、双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等花样繁杂的许多品种。成都的织锦工人很多,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今云南)攻入成都时,就掠走几万名织工。
黄河流域的丝织业,在唐代后期除关内道有衰落趋势外,河南、河北尚能保持前期的盛况。那时,民间普遍都有织机,有所谓:“有时总嫌织绢迟,有丝不上邻家机。”由此可见,作为农村副业的民间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晚唐时代,定州富豪何明远家里就有梭机五百张,俨然是一个手工纺织工厂了,这可能是当时最大的私营手工业作坊。绢是各地都普遍生产的。从民间机户的情形,也可以看出唐代染织工艺的发达情况。
唐代的绢帛,除作为实用品外,还成为货币而广被使用。有用绢帛作为赋税,唐代的租庸调制度,庸和调就是用绢帛来支付的。有作为贡品,如《唐六典》:“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调庸以造焉。”有作为进献,《册府元龟》济军:“韩弘为汴州节度使,元和十三年进绢五万匹。又十四年王师讨淄青,弘进助平淄青二十万匹。”有作为国费,《册府元龟》经费文宗开成元年正月条:“辛酉盐铁使左仆射令狐楚请以罢修曲江亭子绢一万三千七百匹回修尚书省。”有作为军费,《册府元龟》经费元和十年十一月癸亥条:“诏以内库缯绢五千万匹,付左藏库以供军。”有作为赏赐,《旧唐书·高士廉传》:“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赐士廉物百段。”又据《六典·内府令》条:“凡朝会,五品以上赐绢及杂彩金银于殿庭者,并供之。”等等。
唐代的绢帛,在民间也是普遍作为货币使用,以代替日常生活费的支用。
隋唐时期,我国的丝绸除运销到东南亚的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阇(du)婆国(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婆利国(今印尼的加里曼丹或巴厘岛)等地外,还通过海路运销到现在南亚的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新唐书》记载,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在福建泉州、江苏扬州和广东广州等地设“市舶使”,专门管理以丝绸出口为主的海外贸易。
中国丝绸,不仅以它的绚丽夺目闻名于世,而且轻盈菲薄,无与伦比,也为世所罕见。在古代阿拉伯一本游记中,曾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关阿拉伯商人,在广州拜见一位唐朝官员时,忽然发现这位官员的胸口有一粒黑痣居然透过薄薄的丝绸衣服隐约显露出来。他很惊异,“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发花了”?!这时官员问他:“你为什么老是向我的胸口瞧呢?”商人连忙答道:“我在惊奇,为什么身上的一个痣,可以透过双重衣服看得出来?”官员听了哈哈大笑,便拉起衣袖让商人观看,原来这位官员穿了五件丝绸衣服。这个商人对中国四川如此精薄,更是赞叹不已。类似这样关于中国丝绸的故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地到处传播。因而许多外国商人,冒着惊涛骇浪,慕名来到我国广州、泉州等地争购中国丝绸。
古代日本在学习中国丝织工艺的缫丝、纺织、殷人等技术的同时,还继续从中国输入各种高级的丝绸织物。在唐代,往来于东海、黄海之间的日本遣唐使、学问僧,来中国的更多。对于来到中国的日本学者和僧侣,唐政府还专门媒人每年赠给绢绸25匹及四季衣服,以资鼓励。如一个名叫城桑的僧侣,岛国浙江台州,获得了珍贵的“青色织物绫”而归。直到今天,日本著名的正仓院内,还珍藏着我国唐代传输过去的各种绚丽的锦、绫等名贵织物,以及各种夹缬、蜡染等印染品。据《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至今,日本纺织印染技术书籍中,仍大量沿用“绞缬、﨟缬、絁(shi)、罗、紬、绫、羽.......”等唐朝的汉名。
唐代丝织品的品种花式丰富多彩,织造精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技法。
1.锦
锦是多色的多重织物(现称为缎子织),质地厚重,是丝绸中最为鲜艳华美的产品。人们常常用“锦上添花”赞誉那些好上加好,美中更美的事物。
唐代的锦,在艺术上有经锦、纬锦的区别。经锦是汉魏以来的传统技法。多系一种经畦纹组织,它是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则出现了二枚经斜纹织法。它是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织法。纬锦是唐代工人的新创造,大约开始于武则天当政前后。纬锦是利用多重多色的纬线织出花纹。织机比较复杂,但操作方便,能织出比经锦更繁复的花纹及宽幅的织品。新建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猪头纹锦,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新疆劫去的花树对鹿锦,法国伯希和劫去的翔凤纹锦,都是烫的织锦的珍品。
阿斯塔那还出土了唐代前期的经锦。有武德年间(618—625年)的联珠对马纹锦,永徽四年(653年)的红地小团窠锦,对马纹锦和约在公元660年左右生产的狮子凤凰纹锦及蜀锦。这些都是利用经线起花,织出的团窠,团窠外缘是联珠纹,中央是天马或狮子花纹等。这种文艺在唐代织物中是很流行的。相类似的锦,日本法隆寺也保存了一些,其中“四大天王”锦,幅宽四尺余,长八丈余,是现存最大的一段完整的唐锦。锦的正中织一棵大树,树下织出两只狮子,四大天王在四角,两个向外作射状,两个向内作射状;外围织联珠纹,再外织成宝相花和植物纹。从天王所着甲胄和植物纹来看,不仅具有时代的风格,而且是最高的工艺成就。这些作品,不止纹样美丽复杂,在技法上要用许多不同颜色的经线,在制织上没有用纬起花便利,且能织出更繁复的花纹,所以纬锦的发明,是唐代织锦工艺的一大发展。
锦中加金的技法在盛唐已开始流行。
据记载,唐代后器织锦工艺又有新的发展,这时织锦的花样也与以前大不相同。《太平广记》卷257“织锦人”条记载东都官锦坊织锦工人的话说:“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官锦巧儿,以薄技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不重于世”。这说明唐代后期织锦技术,较前期更有发展。
2.绮
绮的织造方法,是素地起二至三枚经斜纹提花。唐绮除本色花外,也有染成红、紫、黄、绿等色的。这类丝织在阿斯塔那和拜城均有出土。阿斯塔那曾发现唐代花树孔雀纹绮,紫色,连环相套,中饰花树,两边有相对的孔雀图案。还有棋局团花双鸟绮,紫色,地为方格纹,中饰团花纹和双鸟纹。拜城则发现有回纹绮,菱纹绮,縠纹绮,等等。在新疆苏巴什古墓中,也曾出土方格纹红绮。
3.罗、纱
罗、纱是斜织,是汉代以来就流行的一种较复杂的织法。罗、纱都是半透明的,也可以用印染来进行装饰加工。
唐代专门在京城长安设立了织罗的作坊。所生产的罗纹丝绸更为精细。当时,有不少诗人把天空中的云与罗相比拟,如李商隐诗中就有“万里云罗一雁飞”的诗句。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唐代白地绿花罗,可以形象地看到唐代织罗的精湛技艺。这块罗的经纬丝细如毫发,光洁的罗面上印着翠绿的枝叶,当微风掠过,轻罗微飏(yang),恰似烟云缭绕,薄雾飘浮。
唐代纱类丝织物的织造水平更比汉代高出一筹。1968年,在新建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绛色轻容纱,与马王堆出土的汉代素纱相比,显得更疏稀,孔眼更大,织造也更精巧。唐代一些贵妇人,生活奢侈,她们“嫌罗不着爱轻容”。“轻容”就是指的纱。这种轻容纱,直到宋代还继续生产,有人记载:“亳(bo)州出轻纱,举止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谓即轻容也。”

 汉服详细介绍
汉服详细介绍 汉服的主要款式 汉服穿着的场合
汉服的主要款式 汉服穿着的场合 西安汉服婚礼古典与浪漫全纪录
西安汉服婚礼古典与浪漫全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