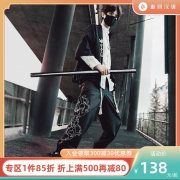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上)
摘要: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方空是形如其方空,吹纶是形如其轻薄。这都说明了当时丝织物的精美。
四川也是丝织的著名产地。《后汉书·公孙述传》有“……蜀地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天下”的记载。四川蜀军成为汉代居第二位的蚕桑基地,蜀锦已逐渐著名,是东汉时代的事。蜀锦的图案纹饰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质地紧密,色泽鲜艳,曾被诗人扬雄称赞为“阿丽纤靡”和“自造奇锦”。蜀锦是以成都地区的产品为最佳,成都又是历史上蜀锦的主要集散中心,因此,成都以“锦城”、“锦官城”而著称于全国。
《盐铁论·本议》有“齐陶之缣”的记载;又据《流沙坠简》记录,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东观汉记》也有:“马援行塞障,到右北平,3诏书赐援钜鹿缣三百匹。”可知定陶、亢父、钜鹿等地都是缣的产地。
又据《流沙坠简》记录,河内是产帛的地区。“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不过这种产品较亢父缣为次。
《庄子计然书》有“白素出三辅,疋(ya)八百”的记载,可知三辅也出产白素。
又据《西京杂记》所记:“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蒲桃锦四匹。”《飞燕外传》也有鲛文锦、紫鸾锦等名目。《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所记“襄邑有黼黻藻锦”。可见汉代丝织花纹是相当丰富的。
汉代丝织花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云气纹
(二)鸟兽纹
云气纹和鸟兽在汉代丝织图案中是常见的,也是汉代其他工艺如铜器、漆器、壁画装饰中所常采用的。这类图案,变化多种多样,也可明显地看出从商、周、战国以来,装饰图案的传统风格。有时,云气纹就是主体图案,更多的是与各种鸟兽、人物穿插布置在一起,表现出缭绕飞卷的形态,构成整个画面的流动效果。鸟兽纹是汉代织绣艺术中对常见的图案。有龙、凤、虎、豹、鹿、鸳鸯、仙鹤、锦鸡、鸿雁、双鱼……等,许多图案中的鸟兽形象、动态、性格,往往被表现的栩栩如生,跃然欲出。
(三)文字图案
用文字作为工艺图案,是汉代装饰的一种特色,多采用吉祥语。如新近出台的几种汉锦,有的织出“延年益寿”;有的织出“长乐明光”;有的织出“登高明,望四海”;有的织出“韩仁绣,子孙无极”,“万世如意”;还有织出“(永)昌长乐”等。外蒙古出土的汉锦,有织出“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八个字,按广成子有万年之寿,用以表示长生之意。有织出“云昌万岁宜子孙”以及“广山”二字的;还有一种织出“君时于意”四字,据考古学家研究,这是表示吐故纳新的涵义。此外,还有织出“群鹄(hu)下”等字的。文句的排列,根据当时织物图案常用的带式单位的横向,由右及左顺序排列。这些文字,都是处于填空的位置,文字本身的美术加工也不很多,但是它们在装饰艺术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织物文字图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所信仰的“谶(chen)纬”,成仙成道,长生不老,多子多孙,万世如意等.........和愿望;另一方面,在某些织物文字中,记载了当时作者的姓名,如“韩仁”、“阳”等,也是可贵的资料。
(四)几何形纹
织物上的几何形纹样是最古老的纹样,远在商、周时代,织奴们就利用经纬变化的织造技术,织出各种形状的几何形纹。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汉代,结合行为仍有听独具的生命力和装饰效果。汉代丝织上的几何形纹,大都构成大菱形两旁附以两个小菱形的组织称为双菱纹。这种纹样组织,也是战国以来常见的一种传统图案。例如战国铜镜背面,就常以这种图案为饰。但在汉代,这种图案的应用更多,在漆器、石刻等工艺上也常常采用。
织物上的这种菱形图案,和其织造方法有着密切关系。汉代的织物,一般是采用一种称为“汉式组织”的斜纹组织,其经纬线的交织点形成斜纹,最适于表现出各种斜纹的菱形图案。外蒙古和山西出土的菱形纹绮,都是这种菱形图案的代表作。在汉代织绣图案中不仅保留了过去传统的菱形图案,而且菱形本身有了多种变化;菱形图案又与其他鸟兽、花叶等纹样结合在一起,以丰富纹样内容,形成统一效果。或以菱形作为四方连续的构成骨法,再在每个菱形中心空间嵌以横向或竖向的对鸟、对兽。此外,在几何形纹中还有传统的雷纹、方格纹、三角形纹、斜方格纹等。
(五)人物骑猎纹等
汉代织绣图案中的人物骑猎纹,大都穿插布置在云气缭绕之中,在画面上占的为孩子也很小,对人物形象没有作细部刻划。但从人物形象或则拉缰立马,或则回身欲射的达的动势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骑猎者的勃勃英姿和生动具体的环境。
为了适应图案题材的扩大和多样性,汉代织绣图案在四方连续构成骨法方面也有了新发展。传统的散点排列、带式排列、几何纹排列等仍继续使用,并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如马王堆出土的440香色地红茱萸纹锦的图案,为一写意花卉和菱形点子结合组成,呈直条形。花朵用块面平涂方法,点子以空心线圈构成连续枝条,并以少量的菱形图案作为点缀。排列虚实结合,疏密恰当,纹样风格和选材都比较新颖。整个画面活泼多变,美观大方。又如云兽缭绕图案,突破了几何式机械并列的形式,而采用横向穿插连续的方法。这种横向的穿插连续,再加以色彩上竖向经条并列的变化,就使画面的整个四方连续效果,显得茂密紧凑,不易辨认带式单位的单调反复;从而在构成上,给人以一种“定体则无,大体则须”的印象。每一带式单位的长度,往往就使织物幅面的宽度、由右向左伸展开去。带式单位与带式单位之间的排列方向,只是一个顺向,所以纹样和文字通常只有一个正向。
汉代丝织品的织造方法。从锦来说都是一种“经丝彩色显花”,即通称为“经锦”的。这种经锦,纬线只用一色,经线则多至三色,由经线显出织物的花纹。三种经线的色彩,一种作为地色,一种织出花纹,一种织作轮廓线。这种织法的图案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
汉代锦的织造组织,既有重经,又有经线彩条的排列变化,因而图案设计的用色,可以多到四、五色,甚至可以有三、四种颜色不受经条的限制而遍地出现。举世闻名的“韩仁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织品。
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时,襄邑等地已出现了织成锦,说明二千多年前我国已有纬起花织锦技术。织成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经断纬而又不同于缂丝。织造时,在平纹或缎纹的底纹上,比经线粗的纬线跨越没有花纹的地方,在应当起花的地方浮于经丝之上,花纹图案显示于织物表面;织物背面的底纹上则横向排列着与正面花纹色彩相同的纬线。图案花纹可不受提花条件下的单位反复的限制,能够织出章法自由的画面,但费工多。
汉代,用通经断纬的织法,织成正反面完全一样的缂丝织物,曾称为“缀锦”。
东汉时,蜀锦的用色,开始有了加金技术,色彩效果更加富丽辉煌。
汉代纹绮,是由一色经线起花,在素地上显出花纹。《说文》:“绮,文缯也。”戴侗(dong)《六书故》:“织素为文曰绮”。汉绮的织法除继承殷代的那种“类似经斜纹组织”之外,在起花部分中的每一根长浮线的经丝及其相邻的另一根经丝,都是平纹组织。
罗是在“纠经”的织机上织出,特别是显花的纹罗,织造更为复杂。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朱罗、皂罗、烟色罗、纹罗绣花丝绵袍和绣罗香囊等。从这些罗织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杯形菱纹提花、几何纹、对鸟纹等生动雅致的花纹。杯形菱纹罗每平方米仅中30余克。一件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的素纱襌衣,重49克(不到一两),一平方米仅重15克。真所谓“轻纱薄如空”,表明二千一百多年前我国缫丝和丝织技术已具有很高水平。
汉代,利用加过强拈的纱线受潮湿后产生绉缩这一规律,有意识地用强拈的丝线织成纱,然后浸水使之收缩而起绉,就成为绉纱。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四块浅绛色绉纱,当时专门叫它为縠(hu)。
绢和缣都是平织的,但缣比绢更为精细。绢的经线和纬线的密度大致是相等的,汉绢的经纬线每平方厘米约有:经 43—46,纬 33—36。而缣是经线密于纬线,汉缣的经纬线每平方厘米约有:经 62—80,纬 35—55。古人诗有云:“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汉代缣以四丈为一匹,可见缣的织造比织绢费工。
在国外,如朝鲜平壤东汉王盱(xu)墓也出土了菱纹罗等丝织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瑟“,弦线直径最细0.5毫米,最粗1.9毫米,经分析是用377根平均纤度为26□(上为代,下为糸)的生丝组成单股丝,再由16根单股丝分别并拈为一根最粗的弦线。这说明我国早在西汉初期,络丝、并丝技术已达很高水平。
4、魏晋南北朝的染织工艺(公元220年——581年)
六朝时的染织生产,从管理机构看,魏晋时仍沿袭两汉旧制,设官营工场专门织造。《晋书·武

 汉服详细介绍
汉服详细介绍 汉服的主要款式 汉服穿着的场合
汉服的主要款式 汉服穿着的场合 西安汉服婚礼古典与浪漫全纪录
西安汉服婚礼古典与浪漫全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