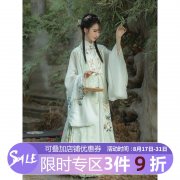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上)
摘要: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东周。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在周代,工艺种类增多,分工更细,青铜器令彝和《尚书》的《酒诰》、《康诰》都有“百工”一词,就是指从事工艺制作的工奴和管理生产的百官。
染织工艺中,养蚕、缫丝、织帛、种麻、采葛、织絺、染色,都有专门分工。
根据《周礼·职方》的记载,当时的冀(ji)州产帛,豫州产丝麻。
在周代,不但设有专职“典丝”官负责管理丝织生产,每年还要由帝王的皇后亲自主持所谓祭祀蚕神的“先蚕”典礼。可以想见当时对蚕丝生产的重视。
根据股东文献和当时青铜器铭文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周的丝织工艺较前代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和提高。首先,由于丝织技术的提高,丝织品的品种较前增加;其次,在丝织品的美术加工,特别是在色彩的多样化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
在品种方面,除罗、帛、纱、绫、绢、绮、纨等丝织物之外,周代末期已出现了锦。《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意思是:“织出贝纹的锦,文采交错,真是华丽”。这是我国最早提到锦的名称。《禹贡》有“扬州厥篚织贝”的记载,“贝”当是指织作贝纹的锦。《诗经》的《郑风》、《唐风》、《秦风》中有:“锦衾”、“锦衣”、“锦裳”、“锦带”等记载。《穆天子传》也有“盛姬之丧,天子使嬖(bi)人赠送文锦”。《国语》载:“齐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陈妾数百,食必良肉,衣必文绣。”《说苑》:“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儿狐裘者,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从这许多记载中,可以知道周代的贵族已以锦绣作为服用。但究竟数量还不太多,就是在贵族中也有认为它是奢侈品和亡国的象征。
3、春秋战国的染织工艺(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770年,周朝平王被迫迁都雒(luo)邑(今河南洛阳),历史叫作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铁器和耕牛的使用和推广,对当时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纺织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诸侯用布帛交往,动辄以十万计。蚕桑的生产遍布祖国各地,丝织品更加精美,陈留、襄邑除的美锦,齐鲁除的薄质罗纨绮缟和精美的刺绣,都著称全国,不仅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工艺上也达到了高度水平。而麻类栽培和纺织更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常用精细的苧麻布作为互相馈赠的贵重礼品。
据《史记》记载:齐国的都城临淄,当时是一个有七万户,二十几万人口的大都邑,城内商店栉(zhi)比,货架上摆满各种布帛、衣服,买卖兴盛。
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呈现出地域性的分工,象韩国的弓弩,吴越的刀剑,邯郸的冶铁,巴蜀的竹木器,临淄的制陶,长沙的锡器,番禹的珍宝,合肥的皮革,都是全国著名的产品。
据《禹贡》等书的记载,这时染织工艺生产的分布大致如下:
一、冀州(在今山西、河北、河南黄河以北、辽宁以西一带),产布帛。《周礼·夏官·职方氏》:“并州......其利布帛。”
二、青州(在今山东泰山北、山东辽东两半岛),产絺、丝、纨、绮绣纯丽物。《禹贡》:“青州贡盐絺海物,岱(dai)献丝枲(xi)......。”《汉书·地理志》:“河东土地平易......作手工业,织冰,纨绮,绣纯丽之物。”
三、兖州(在今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产丝、织文。《禹贡》:“桑土既蚕,□丝木条厥贡漆丝,厥篚织文。”
四、徐州(在今江苏、安徽及山东南部),产玄织缟。《禹贡》“厥篚玄纤缟。”
五、扬州(在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浙江北部),产织、绩。《汉书·地理志》:“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
六、荆州(在今湖南湖北及江西河南一部),产玄练。《禹贡》:“厥篚玄练玑组。”
七、豫州(在今河南大部、湖北、山东、陕西一小部),产丝织纩(kuang)紵(zhu)。《禹贡》:“厥贡漆枲(xi),絺(chi,zhi)紵(zhu),厥棐(fei)织纩......。”
战国染织工艺最发达的,当算齐鲁地区。所谓“齐纨”、“鲁缟”、“卫锦”、“荆绮”,都是全国著名的产品。而齐国的染织生产量也很大,有“冠带衣履天下”的比喻。
据《韩非子·外储说右》记载,战国初期,吴起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出之”。说明当时我国已有控制布幅宽度的织筘(kou)。
①丝织工艺
春秋时代,各诸侯之间赠送的丝织品最多只有三十多匹。到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开展“变法”运动,在“奖励耕织,发展桑麻”政策的推动下,蚕桑生产大发展,缫丝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丝织品产品猛增,当时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的丝织品最高已达千匹以上。
由于蚕桑生产不断发展,在生产实践中也不断创造出新的经验。《荀子·赋篇》中有《蚕赋》:“三俯三起,事乃大矣。”就是说蚕经过三眠,就有上蔟结茧。因此,要抓紧季节,选良种浴茧,促其发蛹成蛾,交配产卵,以提高来年蚕丝的产量和质量。当时的蚕室、蚕架、蚕箔(曲)、受桑器(筐)和缫丝等设备和工具的形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已能织造出许多品种和纹样的丝织物。长沙广济桥五号战国木槨(guo)墓曾出土圆形丝袋、丝带及织锦。丝袋的丝帛经纬密接,异常细腻;丝带则是以斜纱织成规则的网目空花;织锦上织出双菱形内夹小花的图案,是一种用提花方法织造的丝织品。在长沙406号战国墓,曾出土有褐紫色菱纹绸片,黄褐色绸片,及紫褐色菱形纹、犬齿纹迎光变色的丝带。在长沙左家塘等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一批丝织品中,除传统的几何菱形纹锦外,还有“填花燕纹锦”、“对龙对凤”等三色动物纹锦。在苏联乌拉干河流域的巴泽雷克的古墓(相当于春秋时期)中,也曾发现菱纹绢。
值得提到的是1982年1月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大批珍贵的战国时期丝织品。这是我国继马王堆一号汉墓以后在古代丝织品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马山一号墓共出土丝织品二十多件。计有绢地龙凤纹九彩绣衾,彩条动物几何纹锦面绵衾;有绣罗单衣、绣绢单衣、锦面绵衣、绣绢绵袍、绢面夹衣、纱面绵袍、棕色绣卷面绵袍、棕色锦面绵袍,还有棕色锦面夹袱、朱绢绣裤、绢裙、“幎(mi)目”、“握手”、组带、镜衣、木俑身上穿的彩衣、席囊、棺罩、帛画、棺饰绢带和大量小片丝织物。绝大多数丝质衣物形状完整,色泽鲜艳。织物的品种有绢、锦、罗、纱、组、绦(tao)等,还有大量的绣品。在每一个品种内,又是织法多样,色彩纹样各异。从研究价值说,这次出土超过了以往多次战国丝织品的发现。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绢是简单的平纹组织,经纬密度相差较大。有的绢因纬线有规律地或松或紧,呈现出“畦(qi)纹”。一般用作衬里的绢则叫粗疏。大多数绢是白色,也有染作朱红、紫红、黄、浅褐、黑色。在所有丝织品中,绢的用量最大。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龙凤虎纹罗襌衣,罗地略显浅棕色,织法为三梭平织,一梭绞经,经纬密度为46×42根/平方厘米。这种罗孔眼均匀,质地轻盈,用作绣地,可对花纹起明显的反衬作用。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锦,古朴而富丽,有朱红、暗红、黄、深棕、浅棕、褐等色。单幅一般为二色或三色,最多的有六色。为解决织造困难,多色的采取分区法。一般是把两根或三根不同颜色的经线分成两组或三组,用提花方法织成,经组织基本上是三上一下或三下以上。有些经线经过强化,使织物表面形成一道道凸起的织纹;有的还在普通经线外另附挂经。双色锦正反面呈现相同纹样,颜色则不相同。三色锦只有正面呈现花纹。锦的纹样以几何形图案为主题,有棋格、菱形、S形、六边形,其中菱形最富于变化。动物纹为次,有龙、凤、虎、麒麟等,另外还有歌舞人物纹。这些纹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上巧妙的配色,形成五彩缤纷,花纹多变的效果。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质量和图案设计,都充分反映了当时丝织生产技术的高速成就,多数平纹织物结构均匀、整齐,最密的绢比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绢还要细密,与晚一些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绢(经密200根/厘米)相去不远。最能反映出织造水平的是各种锦的织造,就其中三色锦面而言,N4舞人、动物纹锦的幅宽和经纬密度都与西汉时期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锦相近,甚至还要超过。这充分反映战国时期已有较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制造技术。象N4这样的大单位花纹的织锦过去只见于东汉,马山一号墓的发髻,把此类织锦出现年代大大提前了。
从上述出土丝织物及古代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提花技术比商、周已有很大进步。商、周出土的提花织物都是简单的几何图案,变化不多。春秋战国时代的提花织物,开始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出现了比较复杂多变的鸟、兽、龙、凤花纹。但是,最常见,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菱形纹”。除此之外,还有圆圈纹、簇点纹

 汉服详细介绍
汉服详细介绍 汉服的主要款式 汉服穿着的场合
汉服的主要款式 汉服穿着的场合 西安汉服婚礼古典与浪漫全纪录
西安汉服婚礼古典与浪漫全纪录